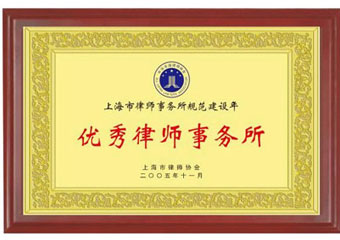在《羅馬規(guī)約》7中,第1條規(guī)定了前南問題國際法庭有權(quán)起訴自1991年以來在前南斯拉夫境內(nèi)嚴重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的人。第2至5條規(guī)定了法庭可以對違反《日內(nèi)瓦公約》的罪行行使管轄權(quán)。第2條包括故意殺害、酷刑、造成嚴重痛苦或傷害、破壞財產(chǎn)、驅(qū)逐、轉(zhuǎn)移或拘留、劫持人質(zhì)和強迫戰(zhàn)俘在敵對部隊服役或剝奪他的公平審判。第3條包括使用有毒武器,對不設(shè)防的地方進行破壞和軍事攻擊,奪取、掠奪、破壞或毀壞宗教、藝術(shù)、科學(xué)或教育機構(gòu)。第4條將 "種族滅絕 "定義為殺害和陰謀、企圖、公開煽動和共謀實施種族滅絕。第5條界定了其管轄范圍內(nèi)的相關(guān)罪行;謀殺、滅絕、奴役、驅(qū)逐出境、監(jiān)禁、酷刑、強奸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基于宗教、種族或政治原因的迫害。
根據(jù)《國際刑事法院規(guī)約》和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的判例法,概述并批判性地討論戰(zhàn)爭罪個人刑事責(zé)任的概念,即行為人是根據(jù)上級命令行事的。個人刑事責(zé)任的概念是從傳統(tǒng)國際法與人權(quán)和人道主義法的合并中演變而來的。 從歷史上看,個人刑事責(zé)任的概念從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后的《1919年凡爾賽條約》2、此后的1945年《紐倫堡憲章》3和隨后的1946年大會4中得到了承認,其中指出,根據(jù)國際法,種族滅絕是一種需要個人承擔(dān)責(zé)任的罪行,1948年的《種族滅絕公約》對此進行了重申。
1991年,國際法委員會制定了《危害人類和平與安全罪法典草案》5,其中特別提到了戰(zhàn)爭罪。前南斯拉夫的事件引起了國際刑事法院的建立,因為1994年通過了《國際刑事法院規(guī)約草案》。1996年對該法規(guī)草案進行了修訂。規(guī)約草案導(dǎo)致1998年通過一次國際會議頒布了《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guī)約》,并于2002年7月1日生效。根據(jù)《規(guī)約》的措辭,該法院的管轄權(quán)僅限于最嚴重的國際罪行,包括戰(zhàn)爭罪。此外,在南斯拉夫和盧旺達發(fā)生的事件導(dǎo)致聯(lián)合國安全理事會設(shè)立了起訴應(yīng)對前南斯拉夫境內(nèi)所犯嚴重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行為負責(zé)者的國際法庭或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前南問題國際法庭)(第808(1993)號決議)和盧旺達問題國際法庭(盧旺達問題國際法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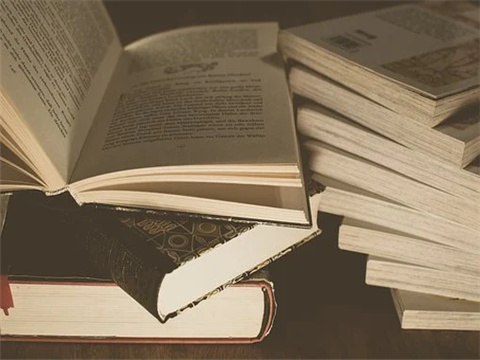
1 國際法。Malcolm N. Shaw p 232
2 第二百二十八條
3 第六條第2(c)款 39 AJIL 1945 Supp p 259
4 第95(1)號決議
5 A/46/10和30 ILM 1991, P 1584
6 第955(1994)號決議
7 《國際法案例與資料》。D.J. Harris第748-750頁
第7條規(guī)定,"計劃、唆使、命令、實施或以其他方式協(xié)助或教唆計劃、準備或?qū)嵤?"第2至第5條所述罪行的人,可被追究個人責(zé)任8。第7條還規(guī)定,被告人的官方職位并不能免除其刑事責(zé)任,也不能減輕預(yù)期的懲罰9。它特別指出,如果上級知道或有理由知道下級即將或已經(jīng)犯罪,而上級沒有采取必要的合理措施防止下級的行為或懲罰下級,那么下級犯罪并不能免除其責(zé)任10。此外,第7條規(guī)定,即使被告是根據(jù)政府或上級的命令行事,這也不能免除他的刑事責(zé)任,盡管這可以被視為法庭的一個減刑因素11。因此,從第7條的措辭來看,非常清楚地規(guī)定了個人刑事責(zé)任的概念,而不論其官職如何,盡管根據(jù)上級命令行事的下屬有可能得到減輕。
自成立以來,前南問題國際法庭已經(jīng)對被指控犯有戰(zhàn)爭罪的個人提出了50多份起訴書。在兩個認罪的人中(另一個是埃爾德莫維奇),塔迪奇被定罪并被判處監(jiān)禁。這個案件12與前南問題國際法庭是否推翻了其處理個人刑事責(zé)任概念的管轄權(quán)的問題特別相關(guān)。塔迪奇以許多理由向前南問題國際法庭上訴分庭提出上訴,包括列舉德國、英國、美國、新西蘭和其他國家違反第3條的例子。在上訴分庭的第13號裁決中,提到了安全理事會14日一致通過的關(guān)于索馬里問題的兩項決議,即實施違反人道主義法的行為者或下令實施這些行為的人將被追究 "個人責(zé)任"。這包括下級和發(fā)出命令的上級。
上訴分庭指出,雖然《日內(nèi)瓦公約》第3條沒有明確提到違反其規(guī)定的刑事責(zé)任,但不能因為沒有關(guān)于懲罰違法行為的條約規(guī)定而排除個人刑事責(zé)任的概念。然而,上訴分庭指出,習(xí)慣國際法對嚴重違反第3條的行為規(guī)定了刑事責(zé)任,在南斯拉夫,根據(jù)《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lián)邦共和國刑法》和1977年的附加議定書以及1992年4月11日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的法令,這種違反行為應(yīng)受到懲罰,因此有關(guān)個人應(yīng)該知道這種行為在國家法院應(yīng)受到懲罰。
8 第七條第1款
9 第七條第2款
10 第七條第3款
11 第7(4)條
12 檢察官訴塔迪奇;[1996] 35 ILM 35;[1996] 2 IHRR 578
13 1995年10月2日,段落。128-129
14 SC第794號決議(1992年12月3日;SC第814號決議(1993年3月26日)。
分庭的結(jié)論是,由于危害人類罪既可以在國際上實施,也可以在國家內(nèi)部實施,因此,在任何一種情況下都可以援引第5條。它指出,如果情況表明已經(jīng)犯下了這種罪行,那么就必須追究個人的刑事責(zé)任,因為正如前南問題國際法庭所說,"違反國際法的罪行是由人犯下的,而不是由抽象的實體犯下的,只有通過懲罰犯下這種罪行的個人,國際法的規(guī)定才能得到執(zhí)行。 "前南問題國際法庭在審查具體違法行為時得出結(jié)論,認為涉及個人刑事責(zé)任,而且不論這種行為是在國內(nèi)還是在國際上實施的,因為人道主義法的原則和規(guī)則在全球武裝沖突中得到廣泛認可。因此,從檢察官訴塔迪奇案中可以看出,上訴分庭準備采取盡可能廣泛的解釋,以包括個人責(zé)任的概念。上訴分庭進一步指出,根據(jù)第3條,前南問題國際法庭對在國際上或在國家內(nèi)部發(fā)生的事件都有管轄權(quán)。它提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對這種罪行的承認以及隨后的《紐倫堡憲章》15和1948年大會決議中對包括戰(zhàn)爭罪在內(nèi)的罪行的定義。分庭認為,這表明國際法和國家實踐承認這些規(guī)則,表明有意將禁止戰(zhàn)爭罪作為刑事犯罪,同時考慮到國家法院和軍事法庭對違反這種罪行的懲罰。
檢察官訴Furundzija案16中指出,人權(quán)條約的規(guī)定要求各國承擔(dān)某些義務(wù),禁止和懲罰實施酷刑的個人,并阻止這些個人通過其官員實施酷刑。人們承認,國際人權(quán)法涉及的是國家責(zé)任而不是個人刑事責(zé)任,但酷刑作為一種刑事犯罪被禁止,應(yīng)根據(jù)國家法律予以懲處。前南問題國際法庭還提到,人權(quán)條約的簽署國有義務(wù)行使其管轄權(quán),調(diào)查、起訴和懲罰罪犯。因此,前南問題國際法庭提到,這些國家的義務(wù)包括并延伸到個人的刑事責(zé)任。前南問題國際法庭進一步澄清說,禁止酷刑的條約規(guī)則的存在表明,國際社會已經(jīng)認識到通過在國家間和個人層面上的運作來取締任何類型的酷刑的重要性。非常清楚的是,同樣從全球條約而非具體條款的角度來看,前南問題國際法庭為任何成員國調(diào)查和起訴被認為特別違反了第2和第5條的個人的行動提供了理由。該案還規(guī)定,"參與酷刑過程的人中至少有一人必須是公職人員,或者至少必須以非私人身份行事,例如,作為一個國家或任何其他擁有權(quán)力的實體的事實上的機關(guān)。" 這顯然包括了根據(jù)上級命令行事的下屬。
15 第6(2)(c)條,(同上
16 38 ILM 317 [1999]
17 《國際法案例與資料》
在另一個案件,即檢察官訴Mucic等人案18 中,上訴分庭指出,第3條沒有必要明確提及個人刑事責(zé)任,以便對違反相關(guān)條款的行為進行刑事制裁。分庭提到了前南問題國際法庭在檢察官訴塔迪奇案中的做法,其中指出,對個人刑事責(zé)任的認定不會因為沒有關(guān)于懲罰違約行為的條約規(guī)定而受到阻礙19。塔迪奇案確立了這樣一個觀點:"國際法禁止的個人行為構(gòu)成刑事犯罪,即使沒有關(guān)于審判違法行為的管轄權(quán)的規(guī)定。"該分庭的結(jié)論是,它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通過刑事制裁的方式在國際一級執(zhí)行違反國際公認的國際人道主義法原則的行為,這些原則已擴大到涵蓋國家間和國內(nèi)武裝沖突的情況下。第20審判庭指出,酷刑行為必須是 "官員或以官方身份行事的其他人所為,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許下所為"。這包括根據(jù)上級命令行事的下級。在Blaskic 21案中,審判分庭指出,違反《規(guī)約》第3條的行為包括違反《海牙條例》的行為,由于其嚴重的性質(zhì),它們非常 "可能引起《規(guī)約》第7條規(guī)定的個人刑事責(zé)任"。分庭還指出,從習(xí)慣國際法的實踐中可以看出,對違反相關(guān)條款的個人進行刑事制裁。
在Kunarac、Kovac和Vokovic 22案中,上訴分庭首先確定了一個觀點,即必須存在武裝沖突,導(dǎo)致行為人在其中發(fā)揮作用并造成犯罪。上訴分庭隨后認為,在考慮犯罪是否可被視為與武裝沖突'有關(guān)'時,可以考慮某些因素,包括犯罪是否作為'官方職責(zé)'的一部分或在其中實施。這顯然涵蓋了下屬接受命令的情況,但并不注重這種人的刑事責(zé)任。總之,從Furundzija和Kunarac、Kovac和Vokovic以及第7條的措辭中可以看出,《規(guī)約》的意圖是涵蓋所有級別的個人,因此,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作為下級接受上級的命令不會成為戰(zhàn)爭罪的借口,這種因素只有在前南問題國際法庭或上訴分庭斟酌后才會被視為減輕處罰的情節(jié)。 深圳南山區(qū)國際法律師事務(wù)所